笔底真趣见精神
——品程里鹏花鸟画里的"鉴藏之道"
文/蔡国声
咱玩收藏的都知道,一件东西值不值当,先看"开门"不"开门"。程里鹏这后生的画,我头一眼瞅着就心里透亮——这是"开门见山"的真,不带半分虚气。不是画室里摆出来的雅,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实诚,像老宅墙根那株野菊,没人侍弄,自个儿从土里钻出来,带着股子经风见雨的鲜活气。这股子劲儿,可比那些刻意做旧的"仿品"金贵多了。
要说他画里的"胎骨",那是真扎实。别人画花鸟,总爱挑些名花异鸟,恨不得沾点"文气"的边,他偏不。农家院墙上的南瓜花、菜畦边的母鸡带崽、晒谷场啄谷的麻雀,全是些眼皮子底下的寻常物。你瞅他画的鸡雏,那小爪子在泥地上扒拉的憨样,干笔皴出来的绒毛,蓬松得像能摸出温度;南瓜花更绝,连虫咬的缺角都不避讳,藤黄点的蕊心稠稠的,活像刚从篱笆上摘下来,还沾着露水和土渣。这哪是画?分明是把皖南田埂的晨雾都收进宣纸上了。咱鉴定老瓷讲究"胎土见真章",他这题材里的"土气",就是最纯的"胎质"——没在田埂蹲过仨月,怎知南瓜花晨开暮蔫的性子?

光有"胎骨"还不够,笔墨里的"包浆"才见功夫。这后生学古人,但不做"复制粘贴"的活儿。画竹,笔锋带点涩,像山涧石缝里钻出来的野竹,竿子不直溜,可那股拧劲透着股子犟气——学了板桥的"写",却没学板桥的"傲",多了几分庄稼人的实在。去年见他那幅《秋菊栖雀》,菊瓣用没骨法晕染,墨色从浅黄到赭红,润得像晨露打湿的瓣儿;雀儿蹲在篱上,喙啄羽毛那点劲,焦墨勾得干脆利落,有徐渭"舍形取神"的影子,却没徐渭那股狂劲儿,多了点"过日子"的稳当。咱玩古董的都懂,仿品学形易,抓魂难。他这笔墨,是把古人的"魂"拆了,掺进自己的"骨血"里,熬出了新滋味。

现在画坛上,不少人要么往"雅"里钻,画得云里雾里,离生活八丈远;要么往"怪"里跑,笔墨还没练扎实,先玩起了花样。程里鹏不凑这热闹,他的画里全是"烟火气"。丝瓜藤绕着竹架缠,瓜垂下来,蒂上还挂着枯花,活脱脱农妇刚摘了俩,剩下的还在架上晃悠;麻雀不画高飞,专画在晒谷场啄谷粒,翅膀半张的机灵劲儿,跟村口老槐树上见的一模一样。这哪是画花鸟?是把皖南的日子一针一线绣在纸上了。咱看老玉讲究"水头见人气",他这画里的"人气",就是最润的"水头"——不像那些装腔作势的"大师范儿",看着就生分。
说到底,艺术品跟老物件一个理儿,经不经得住时光磨,就看有没有"魂"。程里鹏的画,魂里是皖南的风,是田埂的土,是花鸟虫鱼的活气。你现在看,觉得亲切;放个十年二十年再看,照样能闻见皖南田埂的泥香。咱收藏界常说"真东西不怕等",他这画,就是能等、也值得等的"硬通货"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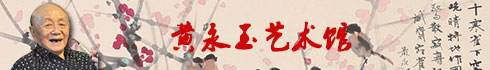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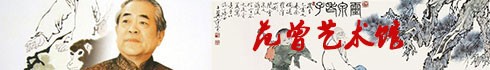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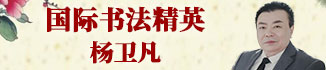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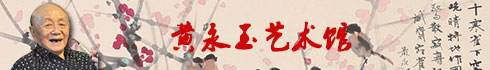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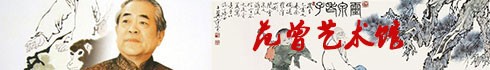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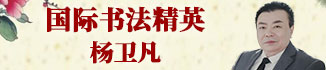


![]()